立春走了迅哥也走了,,清明來了迅哥沒再來,。
迅哥,,清明就要來了,,這幾天一直下雨,,我很想你。
20年前,,我們初次見面,也是一個雨天,,已經(jīng)忘記了在哪里,,是開什么類型的會,,只記得迅哥發(fā)言時大聲說,,今天有收獲,,認(rèn)識了三耳教授,。
那天,不喝酒的迅哥,,喝了5小杯,,我喝了5兩,。
很抱歉,見面前,,我居然覺得迅哥是老弟。
2002年年底,,我從商丘南下湛江,,原計劃潛心教書,,不再寫報刊評論,。不料次年暑假后開學(xué),,晚報一位瀟灑女記者上門,,為副刊約稿,,見面不說話,,摸出一瓶白酒,,一分為二,。我就斷斷續(xù)續(xù)寫了幾篇千字文。那年10月19日,,魯迅忌日,,我把一段講義——“魯迅研究”課的結(jié)束語整理出來,,一看近三千字,,太長了,,就發(fā)給了湛江日報副刊信箱,,記得題目叫《魯迅的意義》,。結(jié)尾是用魯迅逝世4周年時郭沫若的話:“魯迅是奔流,是瀑布,,是急湍,,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海,;魯迅是霜雪,是冰雹,,是恒寒,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春,?!?/p>
10月26日,,一個陌生電話打來:“是宋老師嗎,?我是日報文化版編輯陳迅,,你的文章今天見報啦,我一個字沒有改!”
他聲音雖然有點沙啞,,不太標(biāo)準(zhǔn)的“粵普”,,但比較洪亮,我以為是中年編輯,,表示了感謝,,答應(yīng)繼續(xù)寫稿。
那次開會一見如故,,說的幾乎全是雜文界的事情——他的不少作者,、熟人我也熟識。我在《大河報》也是編評論版,。
第二天,,我到圖書館,找到他的《迅口開河》專欄,,一口氣讀了十幾篇,,明白了他的仗義執(zhí)言與文字功底。后來認(rèn)識了報社河南老鄉(xiāng)夢秋和她的閨蜜金鳳,,隔三岔五一起吃頓便飯,,云天霧地聊一陣,很是爽快,。
不管在哪里吃飯,,迅哥很少打車,自行車是他的標(biāo)配,。他是地道的土著,,長得很普通,,不像作協(xié)的頭頭,,像大隊會計。他笑得很孩子氣,,與他文字的老到判若兩人,。
2013年11月,晚報編輯策劃了一個類似“鏘鏘三人行”的對話式的評論版,,讓廣西民族大學(xué)在讀研究生小陳主持,,我和迅哥做發(fā)言嘉賓,,記得是每周一次。于是我們有了不斷見面的機會,,有時候也不見面,,是把評論文字?jǐn)n在一起,分層次變?yōu)榱奶臁?/p>
那一陣子,,北大畢業(yè)生賣豬肉與擇業(yè)觀念,,政務(wù)網(wǎng)站如何便民利民,體育如何向“群眾性”傾斜,,“回家過年”為什么引發(fā)恐懼,,趕“消費盛宴”值不值得,如何保證“破格提拔”公平性等社會熱點,,都成了我們的話題,,有時候爭得臉紅脖子粗。
但是,,也正因“切磋”得多,,迅哥憂國憂民的赤誠、思想的銳利和談鋒的勁健留在了我的心底,。例如有一陣網(wǎng)上流行不大文明的“屌絲體”,,他認(rèn)為很粗鄙,是生活平庸,、感情空虛的宣泄,。我說,對有些新詞語應(yīng)該稍加寬容,。沒有生命力的東西,,自己也會偃旗息鼓,。例如白話文,,當(dāng)初被復(fù)古派稱為“引車賣漿之流”的土話,后來還是登堂入室,。他不同意,,引用孟子,說:人必先自侮然后人侮之,。不可以“爛鍋不怕摔”地去放大,、展示丑陋。
再后來,,報刊審讀員老周不幸馭鶴,,市文廣新局讓推薦一位對報刊比較熟悉的退休專家,我推薦了迅哥,。開始有議論,,說迅哥不是高級職稱,,是不是找個編審。我解釋,,報社不是高校,,教授一抓一把,關(guān)鍵是對報紙的采寫編評熟悉就行,,不少新聞英語或者傳媒管理學(xué)教授,,恐怕連二三百字的“本報訊”也寫不出來。就這樣,,我們又能夠兩三個月見一次面,,噓寒問暖。
最有印象的一次,,是2015年國慶節(jié)過后,,開審讀會,集中說抗擊臺風(fēng)“彩虹”,。他頭一句就說:“今天差點見不到諸位,。”原來他家陽臺的玻璃門栓不緊,,15級颶風(fēng)襲來,,他和老伴只好用毛毯護住陽臺門,夫婦再用身體頂住毛毯,,前后一個多小時,,累得幾乎虛脫。我說:“你逃跑呀,!玻璃爛了多危險,!”他說一旦頂住了門,就忘記了還能跑,。
記得2017年,,我回老家商丘工學(xué)院執(zhí)教,順便照看母親,,走之前,,我們還在一家小飯館里見面,說好了“茍富貴,,莫相忘”,,回來就聯(lián)系。不料那竟是最后一面,。
今年2月初,,幾位報社朋友告訴我:迅哥走了。我不相信,,他才70出頭,,那樣有生命激情,,整個港城都有他的自行車的輪印,怎么可能呢,。后來看到日報副刊上何銀華老師的《迅哥其人》,,確信他走了,確信他的音容笑貌已經(jīng)是歷史,。
如今,,迅哥走后第一個清明就要來了。我不知道說什么,,不知道怎樣說,,只知道再也聽不到迅哥用沙啞的聲音指點江山、激揚文字了,。
清明來了,,乍暖還寒。迅哥,,你在那邊保重,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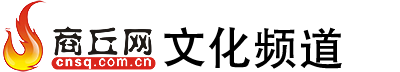


 商丘網(wǎng)
商丘網(wǎ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