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廖天元
一大早,,我就沒看到阿黃,。
平常的時候,我剛走到曬壩,離家還有五十多米,,阿黃就叫喚起來。叫聲響亮,、清脆,、高昂,和見到陌生人那種急促的吼完全不同,,它一定在激動地告訴母親:我回來了,。
這是眾多家養(yǎng)土狗中的一只土狗。母親喜歡養(yǎng)狗,,打小家里仿佛都有狗的存在,。母親養(yǎng)的狗,都是清一色的黃色土狗,,都被沒讀過書的母親叫作阿黃,。狗狗們秉性不同,但我只要喊一聲阿黃,,它們都會對我搖頭擺尾溫柔以待,。
這只土狗,被母親拴在一棵枇杷樹下,。枇杷樹一丈來高,,像瓷碗一般粗細,常年青幽幽的綠,,樹冠鋪展開來,,遮住了小院一半陽光。母親請木匠在樹下給阿黃搭了一個窩,,上面用青瓦蓋著,,下面墊著厚厚的谷草。我看著阿黃在里面打滾轉圈,,顯得綽綽有余,。
我不在家,父親去上班,,阿黃乖乖巧巧陪著母親,。母親去干活,它就守家,。母親一回來,,我看到過它前腳搭在母親身上,像孩子一般撒嬌,。
農(nóng)作的艱辛,,在那一刻化為母親臉上褶皺的笑容,。我大致可以下個結論,母親離得開兒女,,習慣兒女長大后“無情無義”地遠走高飛,,但是一定離不開這條討巧忠誠的土狗。
到了老屋不得不拆的前兩天,,母親和父親失眠了一夜,,決定把狗送給舅媽。在電話里,,母親說了很多阿黃的好話,。舅媽將近八十,慈眉善目,,說一定把狗當自己娃,。母親又叮嚀了幾句,把舅媽惹得有點火,,說不放心就不送過來,。母親笑,趕緊說放心放心,。
下面的敘述依然來自母親的絮叨,。母親說,她在夜間把阿黃的繩子解開,,暗暗發(fā)誓,,如果阿黃就此走掉,那從此就一別兩寬,。哪知第二天開門,,阿黃乖乖地趴在門口。她給阿黃重新套上繩子,,早飯后把它送給舅媽,。
到舅媽家,要翻過三四座山頭,。母親說阿黃在前頭跑得很快,,連一泡尿都沒撒。母親有些猜不透,,是不是阿黃認為母親在和它趕個場,,一會又會和它一起回來。
母親把狗拴在舅媽家的竹林邊,,悄悄瞇瞇地轉身了,。天黑躺在床上的時候,接到舅媽的電話,,說狗不見了,。父親和母親一個翻身,,打著電筒就往舅媽家里趕。兩個老人一句話都沒說,,夜間的風,,只留下他們的長吁短嘆。
母親站在舅媽家里一聲聲呼喚阿黃,,直到聲音有些嘶啞,。那個夜里,阿黃一直沒有出現(xiàn),,倒是村里的狗叫聲此起彼伏。
第二天,,狗還是回到舅媽家里,。舅媽說,阿黃就像一個犯錯誤的孩子,,一直耷拉著腦袋,。母親聽得老淚縱橫,趕緊掛斷電話……
想起來世事真是輪回,。三十多年前,,妹妹出生,當夜被父親抱去舅媽家,。那一年,,我九歲。那一夜,,我一路提著收音機,,預備妹妹哭出聲來時扭開開關。我不知道母親在送阿黃的時候,,是否想起三十多年前送妹妹的情形,,雖然那個場景她沒有親歷。
哪怕有一絲可能,,我想母親絕對不會把阿黃送走,。老屋馬上拆除,而新屋地基剛剛確定,。父親和母親,,要守著建房,也只能在他人家里暫住,。一只土狗,,實在沒有它的立足之地。
有一年我去農(nóng)村走訪,,看到一個老人和一條狗,。那是冬至時節(jié),,微弱的陽光輕輕照在老人臉上,他腳下趴著一只土狗,,畫面安靜得可怕,。我無比酸楚,知道這個老人的風燭殘年,,大部分日子其實只有這只狗相伴,。好害怕自己老了,也是這個模樣,,甚至身旁狗都沒有一只,。
我知道在農(nóng)村,狗真的不僅僅是狗,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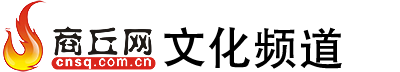


 商丘網(wǎng)
商丘網(wǎng)